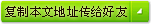一个摩仔与一位护士的故事 (6)
梦想
同是四川人,同是来广州寻找梦想。她比陈国文晚来10年,陈用了十多年时间都没有摆脱城市边缘状态,她只花了3个月
穿过让李林心怯的那条僻静马路,绕经一片工地,迎面是一个破败小村落,它似乎被急切扩张的广州城遗忘多年。菜地尽头,就是陈国文和8户老乡租住的3层旧式砖房。
广州的冬阳照进院子里,是个适合“摆龙门阵”(四川方言,聊天的意思)的天气,但一个女人尖锐的嗓音打破了宁静。她是清远人,受房东之托看管这个院落,也是10家租户里唯一讲白话的人家。
她怒气冲冲地责问一个男子是否打了她的儿子,男子除了骂一声“鸟”外,不屑与之争论。但她激起了四川女人们的公愤,低声讨伐说,“她一直看不起我们”,“其实她不也是外地人吗?”
继而,大家纷纷罗列出各自在这座城市遭受的歧视。张林妻子说,她来广州做环卫工近10年,过年过节发的东西越来越少,工资也没有达到784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她妹妹、唐洪妻子也是环卫工,一次不慎把水溅在一名妇女脚上,被骂得泪水涟涟。她说:“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凭本事找钱,还是被本地人看不起。”她把一大原因归咎为不会讲白话,“我嫂子会讲,别人看她的眼神就不一样。”
陈国文妻子一向轻言少语,这次也加入倾诉队伍,说工厂老板想提她做领班,但她文化低,不会做报表,当面被老板刻薄一番,“那个滋味真难为情,我就希望女儿能读好书,不要像我这样。”
男人们的话题则是跟“制度”有关。一人说,他曾因没带身份证两次被收容,花了600元才赎出。陈国文说,一天晚上,十多个人闯进他家,把他妻子身份证搜走,逼迫他们办理暂住证。
同是四川人,同是来广州寻找梦想,李林却几乎体会不到他们的这些内心苦楚。她一来广州,户口就跟着迁来,所有社会保险齐全。她比陈国文晚来10年,陈用了十多年时间都没有摆脱城市边缘状态,她只花了3个月。
此后,李林恋爱、结婚,享受爱情的幸福。在家人协助下,她离开拥挤的集体宿舍,把生活搬进一个挖有人工湖泊和溪流的大型住宅区,一套125平米的三房,客厅是陈国文出租房面积的两倍。她和丈夫的月入加起来,已经达到这个社会万众渴望的中产阶级标准。
工作上,李林也开始崭露头角。她很快被提为护理小组长,率领护士、试工护士和实习生各一名。她所在的科室被评为全省青年文明号,她被推为号长,下有一名副号长和一名秘书协助。她的甜美笑容出现在病房里,一口流利的白话很能哄得这些平均70岁的病人开心,他们都亲热地喊她“李姑娘”。
就像对广州的每个角落了如指掌,却依然无法感受这个城市奥妙一样,陈国文搭载李林3年,在医院和住宅区穿梭来回,也对李林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因为那显然不是他的世界。李林同样如此。有时她会好奇地打听这些老乡的生活,但一直不曾走进他们家里去看看,虽然陈国文的住处离医院只有400米远。
双方甚至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这不重要。他们只是一种简单的老乡关系。一天夜晚,陈国文走进这家医院,为妻子能得到第二天的专家门诊而通宵排队。他没有找李林帮忙,担心引起对方的反感。
双方其实有意保持一种距离。李林坐在摩托上,把挎包放前面,既是应对潜在凶险,也是在分隔两个人的近距离相处——它不是LV品牌,足够普通,却足够在咫尺之间的两人中划一道鸿沟。她总觉得摩托仔递来的头盔很脏,带着街头的风尘和底层的汗臭,要用餐巾纸擦了一遍才会戴上。
这个距离其实是贫富分化背景下,两个正在分离的阶层之间的关系:看似挨得很近,其实隔得很远。
广州是一座公认比较宽容、平等、低调的城市,富人们穿着休闲服,抽与陈国文一样的6.5元一包的本地烟,不少白领住在城中村内,乘摩的上下班、约会和吃大餐。但近年来,陈国文仰头看到,一群群以“财富”、“荣耀”、“帝景”为标榜的楼盘拔地而起,用围墙把身边鄙陋的城中村隔开。
城市的政策制订者也渐渐不喜欢他这样的穷人,或者说,他们认为这个城市已经没有穷人。这个冬季,先是传出“限制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城”的声音,接下来全城禁止电动车和摩托车通行,据说得到了广大市民尤其是白领阶层的欢迎。
李林的女同事们对禁摩的心态很复杂,终于不见令人胆寒的摩托,但走过医院门前那条马路去公交车站,又让她们担心遭到其他形式的抢劫。“那些被摩托飞车抢过的同事,后来反而都选择摩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搭客仔是让人放心的。”李林说。
|
0 顶一下 |  对一个摩仔与一位护士的故事发表评论 对一个摩仔与一位护士的故事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