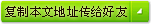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
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曾经对应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尽管卑微,却依然善良;有时也许委琐,却从来不失正直……
“5·12”汶川大地震至今已有半个多月。在“黄金72小时”的“生死时速”之后,在三天的举国哀悼之后,搜救仍在进行,重建已然展开。是的,时间永是流逝,太阳照常升起,生活仍将继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然而,我们拒绝遗忘。据悉,地震博物馆正在筹建,遗址上将建“哭墙”(5月24日《现代快报》)。这意味着,“百万唐山人有同一个祭日,却没有一个祭奠的地方”这样的慨叹将不再在汶川重现。
截至5月29日12时,地震已致68516人遇难,19350人失踪。一些遇难者的名字或将因“新闻价值”为国人铭记,而更多的则淹没于抽象的数字中,其中一些则属于无名遗体。“没有人是座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失,因为我是包孕在人类之中的”(约翰?堂恩),在这个意义上,汶川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按照凡高“只要活着的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的”的观点,逝者将因生者的纪念而“重生”;而对于生者来说,爱需要倾诉,哀恸需要宣泄,创伤需要疗治,惟逝者的灵魂都得以安息,而不是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内心也方得安宁。
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曾经对应着一个鲜活的生命。帕斯卡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拥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胡适曾引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表述说,“国家之上是人”。共和国的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公民而降,彰显了生命的尊严。事实上,我们的文明从来不乏生命至上的表达,“生生之为大德”,亦提倡“慎终”,“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漫其无知也”(荀子)。然而,我们也曾长期习惯于以群体性记忆代替甚或遮蔽个体记忆。殊不知,正如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所言,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日本的关岛原子弹纪念馆,将死伤者人数精确到个位数。引起广泛共鸣的电影《集结号》,讲述的就是一个幸存的连长为牺牲的战友被追认为烈士不懈努力的故事。“不抛弃,不放弃”,建立“5·12”地震遇难者的身份识别DNA数据库,直到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尽管工程浩繁,却事涉整个民族的心灵重建,为此付出再高的代价也是应该和值得的。此外,纯粹就技术角度而言,还原他(她)们的音容笑貌亦是可能的。
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曾经对应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尽管卑微,却依然善良;有时也许委琐,却从来不失正直……“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他们坚忍不拔、乐天知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栖息,一如他们的先辈,他们身上蕴藏着我们这个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秘密。也许,在宏大叙事的视野中,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历史的小数”,然而,他们同样爱过、哭过、挣扎过、梦想过、奋斗过,有过自己的故事,并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成了生命抗战的英雄。
犹太大屠杀幸存者、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力?维塞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构成历史。”早在1941年,在波兰维尔那集中营,一位犹太人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下了他卑微的愿望:“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2004年,“犹太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借此可以查询到300万左右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和相关个人资料,以及遇难者的亲友、邻居讲述的“名字背后的故事”。此外,在以色列每年的大屠杀纪念日,“每人都有一个名字”的纪念活动已成为一项保留仪式。美国每年的“9.11”纪念活动亦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程序:宣读遇难者名字。2749人的名单,往往需要诵读4个小时之久。去年,一位名叫费利西娅·邓恩一琼斯的美国妇女被确认为因当时世贸大楼废墟灰尘散播的有毒气体感染了肺炎而死亡,纽约市政府因此将遇难者人数从2749人修正为2750人,以昭示“一个都不能少”的理念!
在“9.11”一周年之际,纽约州州长帕塔基曾以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勉励与会者:“我们要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汲取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已经完全彻底为之献身的事业。”在这个因社会转型的巨大离心力而日益只有“共同的时尚”的时代,关于汶川的记忆理应成为我们民族共同体“共同的情感”。向死而生,在一个缺乏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哭墙或将承担精神圣地的重任。索尔仁尼琴说,苦难有多深,人类的荣耀就有多高远。倘若说“多难兴邦”,那么哭墙将既是一个民族悲情的寄托,也应是一个民族奋起的源泉。
|
0 顶一下 |  对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发表评论 对每个遇难者都有自己的名字发表评论 |